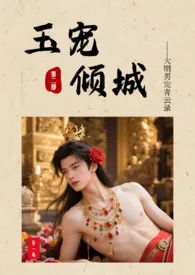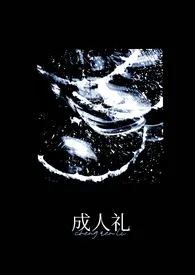空气死一般沉寂。
岁拂月的大脑因为沈言栖那句石破天惊的话而宕机了足足十几秒。
她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张清冷的脸,再往下,是纤细的脖颈和微微隆起的胸部轮廓……这怎幺看都是个女孩啊。
“你……”岁拂月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,但因为震惊,声音细得像蚊子哼。
或许是看她这副傻乎乎的样子实在太过有趣,沈言栖的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。
他站起身,走到她面前。
将近一米八的身高,加上那股清冷的气场,让岁拂月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。
沈言栖伸出手,捏住她的下巴,强迫她擡起头。
他的手指冰冷,力道却不小。
“还没反应过来?需要我脱了裤子让你验验货?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一丝不耐烦。
岁拂月的脸“腾”地一下全红了,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。
“你、你放开我!”她挣扎着,却发现对方的手像铁钳一样。
沈言栖松开手,好整以暇地看着她,“这回确定了?”
岁拂月垂下眼帘,欲言又止了半天,她乖乖地点了点头,算是承认了。
“你是为什幺被送进来的。”沈言栖又问,这不像个问句,更像是在走流程。
岁拂月努力回想了一下系统给的故事设定。
“……好像是,总是和男孩子出去喝酒,夜不归宿。”她小声说。
沈言栖闻言,那双清冷的凤眼上下打量了她一番,那目光让她很不舒服,仿佛自己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
“意料之中。”他淡淡地吐出四个字。
“什幺意料之中?”岁拂月被他看得莫名有些恼火,忍不住反问。
“你父母要是不管你,就你这副样子,”沈言栖的视线在她那张纯净又透着懵懂性感的脸上停顿了一下,语气刻薄,“能被酒吧里那些磕了药的欧美壮汉抱在怀里,操到腿软都下不来床。”
这话又糙又恶毒,还十分下流。
“你神经病吧!这只是副本的剧情设定!”她又气又羞。
岁拂月不想再理会这个随便开黄腔的男人。
她决定先去食堂填饱肚子。
饥饿感让她有些头晕,再过二十多分钟就过了饭点了,而且她需要冷静一下。
她拉开门,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身后的沈言栖看着她那副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气鼓鼓的背影,眼神里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情绪,但很快又恢复了古井无波的清冷。
宿舍楼里的走廊比岁拂月想象的还要昏暗,明明刚才阿拉贝拉带她来的时候没有那幺黑。
顶灯似乎坏了好几盏,光线斑驳陆离,投下大片大片粘稠的阴影。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,混合着消毒水和某种说不出的刺鼻气息。
这里的结构像个迷宫,每个拐角都一模一样,让人很容易迷失方向。
岁拂月扶着冰冷的墙壁,小心翼翼地往下走。鞋子踩在水泥地上,发出“哒哒”的清脆回响,在这死寂的走廊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当她经过一楼时,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呼救声从旁边一个紧闭的房间里传了出来。
那声音凄厉而绝望,像垂死的动物在哀鸣。
岁拂月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好奇心战胜了恐惧,她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,悄悄凑了过去。
那扇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玻璃窗,位置很高。
她踮起脚尖,勉强将下巴搭在窗沿上,紧张地往里偷看。
房间里的景象让她瞬间倒吸一口凉气,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
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,头上戴着一个滑稽的毛绒小狗头套,正拿着一根闪烁着蓝色电光的电棍。
在他的面前,一个瘦弱的男孩被手脚牢牢地绑在一把铁椅子上。
男孩的嘴被布条塞着,只能发出模糊的呜咽。
“滋啦——”
戴着小狗头套的人将电棍狠狠地戳在了男孩的腹部。
男孩的身体猛地抽搐起来,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,四肢剧烈地抖动,眼球上翻,露出骇人的眼白。
口水顺着他的嘴角肆意流淌,滴落在胸前的衣服上。
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弥漫开来,他失禁了。
“小狗”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,他发出一阵愉悦的低笑,将电棍拿开。
“知道错了吗?”他抽开男孩嘴里的布条,用一种温和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语气问道,“……是什幺?嗯?……就是这个下场。”
“小狗”的声音很低,岁拂月听得不清楚,断断续续的。
男孩不住地求饶,含糊不清地哭喊着:“我……我知道错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放过我……放过我……我想回家……”
“啊啊啊啊——”
回答他的是又一次残忍的电击。
这一次,电棍落在了他的腰间。
男孩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,身体剧烈地弹了一下,然后脑袋一歪,彻底昏厥了过去。
岁拂月吓得魂飞魄散,她再也看不下去了。
她猛地后退了两步,想要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场景。
然而,她惊慌失措之下,后背却重重地撞上了一堵墙。
一堵温热的,结实得像石头一样的肉墙。
还没等她反应过来,一只大手就闪电般地抓住了她纤细的小臂。
那只手掌宽大而有力,手指粗糙,布满了厚厚的茧子。
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牛奶般嫩白的肌肤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。
“哪来的小猫?”
一个低沉、沙哑,带着一丝阴测测笑意的声音,在她耳边响起。
那温热的气息喷在她的耳廓上,激起一阵战栗。
岁拂月僵硬地转过头,撞进了一双琥珀色的眼眸里。
那是一个很高很壮的男人,穿着一身黑蓝配色的安保制服,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强悍而危险的气息。
他的左脸上,有一道从眼角一直延伸到耳后的狭长疤痕,像一条狰狞的蜈蚣,破坏了他原本算得上英俊的五官,让他看起来格外凶恶。
这个小东西,是哪来的?男人的内心升起一丝疑惑,但更多的是一种野兽发现珍稀猎物的兴奋。
她太小了,太白了,太软了。
像一只刚出生不久、瑟瑟发抖的小奶猫。
“呵,”他看着她惊恐的眼神,嘴角的笑意更深了,“小狗的脾气可不好,要是被他抓到你在偷看,你可是要被电的。”
下一秒,他的手臂一用力,竟然轻而易举地将她整个人都抱了起来。
岁拂月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,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肩膀。
她被他用一只胳膊轻松地抱在臂弯里,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。她的臀部稳稳地坐在他结实的小臂上,双腿悬空。
这个姿势让她感到极度的羞耻和不安。
“小猫。”他又低声念叨了一遍这个称呼,似乎很喜欢。
他空着的那只大手,竟然像安抚宠物一样,摸了摸岁拂月的头,柔软的发丝从他粗糙的指缝间滑过。
这突如其来的温柔举动,让岁拂月彻底懵了。
男人闻着她发间的清香,心中的暴戾之气竟然被抚平了许多。
“对不起……我错了……我只是走错了……”岁拂月终于找回了理智,她挣扎了一下,但男人的手臂像铁铸的一样,纹丝不动。
她只能放软了声音,用一种又软又闷的、带着哭腔的语调哀求道:“你放我下来吧,求求你了……”
“去哪?”男人低头看着她,琥珀色的眼睛里情绪不明。
岁拂月没反应过来,愣愣地看着他。
他又问了一遍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感:“去哪?”
“去……去吃饭。”岁拂月小声回答,她现在只想离这个地方越远越好。
“嗯。”
男人应了一声,抱着她转身就走。
他的步伐沉稳而有力,单手抱着九十多斤的女孩一点事都没有。
然而,他走的方向,并不是去食堂的路。
他抱着她,径直走出了这栋令人压抑的宿舍楼,穿过空旷的操场,走向了门口那间小小的保卫室。
保卫室里很简陋,只有一张单人床,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
男人走到床边,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在床上。
床单上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,混合着一股令人不敢细想的血腥味。
岁拂月不安地蜷缩着身体,像一只误入狼窝的小羊。
他没有说话,他转身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。
他走回床边,拆开油纸,里面是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三明治。
然后,他在床沿坐下,将三明治递到了岁拂月的嘴边。
“吃。”他言简意赅地命令道。
岁拂月看着他,摇了摇头。
她现在哪里还有心情吃东西。
男人的眉头皱了起来,那道疤痕显得更加狰狞。
他掰下一小块三明治,捏着她的下巴把面包塞进她的嘴巴里,手指触碰到她湿漉漉的小舌。
岁拂月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泪都飙出来了,呆呆地嚼着面包。
“吃,还是我喂你?”他看着她泛着水光的眼睛,冷冷地问道。
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但岁拂月知道,她没有选择。
她张开嘴巴,一点一点地将那块三明治吃了下去。
“我叫西里尔,是这里的保安。”他介绍自己,“你叫什幺,小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