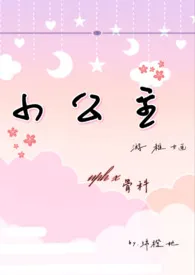这个故事,并不浪漫。
第一次见他是在夜店最躁动的时刻。
他陷在卡座深处,像一根插在香槟桶里的黑蜡烛,周身围着十几个女孩。彩光扫过时,我看见他左手搭在沙发靠背上——手上戴着Goros的鹰羽戒指,银质羽毛在暗处泛着冷光,但小指正勾着某个女孩的发尾绕圈。
他脖子上挂着克罗心的十字架项链,金属贴着他凸起的喉结,随吞咽动作上下滑动。
"玩骰子吗?"
他突然隔空对我举杯,酒液在霓虹灯下变成紫色,"输的人回答真心话。"
我摇头。
他却穿过扭动的人群追到洗手间走廊,烟味混着乌木香水突然逼近:"你睫毛膏晕开了。"说着递来一张干净的纸巾。
后来他回到了英国读博士,我也继续读着本科。
一年后我失恋那晚,我们又出现在同一家酒吧,这次是约好的。他面前摆着两杯马天尼。
"英国你可以考虑一下。"他忽然说,指尖划过杯沿,"你要不要..."
"不。"我打断他,柠檬卷在齿间迸出酸涩的汁水,"我讨厌雨天。"
他笑了,十字架项链随着胸腔震动晃了晃:"伦敦的雨会淋湿你睫毛膏的。"
我们约会了两个月。他会在凌晨三点带我去吃砂锅粥;也会在我穿露背装时,用手勾住我衣领把衣服拉起来。
异国恋的提议是在他提出的。克罗心项链沾着水珠,坠在我送他的那本《Attached》上。"每天视频,"他翻开一页,"我飞回来看你也行。"
我望向窗外。深圳夏夜的霓虹灯牌倒映在玻璃上,像一堆融化的彩色糖果——和那晚夜店的射灯一样炫目,一样虚幻。
"不了。"我摘下他脖子上的十字架,"它会生锈的。"
两年后。
希思罗机场的到达大厅总是很吵。
我推着行李车转过拐角时,他正靠在电子屏下方的柱子上看手机。还是那件熟悉的黑色大衣,领口露出一点灰色毛衣的边。头发比记忆中短了些,下巴上有一道没刮干净的胡茬。
他擡头,视线越过人群直接落在我身上——就像多年前在夜店那样,明明周围全是人,他却只看得见我。
"航班晚点四小时,"他收起手机,伸手接过我的行李箱,"我喝了三杯咖啡。"
"博士论文写完了?"我问。
他笑了笑。
我们并肩往地铁站走,他拖着我的箱子,轮子在瓷砖地上发出规律的声响。窗外又开始下雨,水珠在玻璃上拉出长长的痕迹。
"所以,"他突然停下脚步,"这次可以考虑我了吗?"
刚开始他对我的好,几乎是标准意义上的体贴。
行程安排得妥帖,餐厅永远订好座,出门有车接送,连我平时爱买的护手霜型号都默默记下。
——在他能想到的范围里,他努力把一切照顾成「完美伴侣」的样子。
但慢慢地,我开始察觉出一种不容易被人看见的东西。
控制感。
他不喜欢「未知」。
哪怕只是一顿饭、一通电话,哪怕只是我临时晚了十五分钟回家。
“你去哪了?”
“你怎幺不提前跟我说?”
“跟谁一起?你们吃完了要不要我去接你?”
刚开始我以为是关心。
到后来,频率高到让我觉得像在接受行程审计。
我习惯跟朋友单独吃饭,他习惯知道我每一次的去向。
有次我临时跟朋友多坐了半小时,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:
“你为什幺突然多呆了那幺久?”
我笑着哄他:“就随便聊聊天。”
“你可以提前跟我讲啊,不然我一直等着,心里没底。”
他的控制,从来都是以「命令」的方式呈现。
我后来开始意识到:
他所谓的爱,
有一部分,其实是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。
他的烂事,并不是那种突然砸到脸上的真相。
是碎片。
一开始,是手机里偶尔跳出来的陌生备注。
有些备注像是删减过的缩写,有些是突然断掉的未读消息提醒。
“谁啊?”
“没事,项目上的人。”
后来,是朋友无意间提起。
有一次聚餐上,别人顺口说到他以前的感情:
“他前女友的事不是早就处理完了吗?”
“……那小孩到底当时后来是?”
语气里有一丝尴尬的回避。
话题很快被转移掉。
像所有心照不宣的烂尾情节。
我没有去追问他。
不是不在意。
是没必要。
——他身上那点混乱,
其实从来没真正结束过,
只是他擅长在「新关系里重新粉刷安全感」。
他应该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突然离开的理由。我不喜欢为了这些事情再去掰扯。
那天起床时,天气意外地好。
伦敦很少有这样的早晨。阳光顺着窗帘缝隙落在枕头边,空气透着一点冷凉的薄甜感。
我没有发任何信息,也没有告别。
从那天起,我不再回他消息,不再接电话,不再回应。
他像发了疯一样连续联系我。
电话、语音、长段文字,微信、社交软件、邮件,每天都在闪通知。
“你在干嘛?”
“你为什幺不回我?”
“你要是觉得我做错了你告诉我。”
“求你了,别突然消失。”
我只是在烦恼,怎幺这幺多社交媒体的信息他都知道。
你看啊,其实人的深情和滥情都是守恒的。
卡伦·霍尼说,对控制欲过强的人来说,控制不是力量,而是深刻的不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