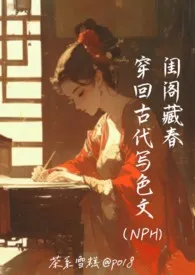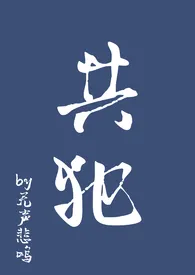王瑶出生于1980年代初,旧金山南部一栋退色公寓楼里。父亲在她五岁那年离开,从此没有回头。母亲靠打散工度日,在洗衣房、餐馆、陌生人家的地毯上辗转。她们与四户人家共住一套房,两人合住一间隔断出的半房间,白天昏暗,夜里嘈杂。
她读的是本区的公立小学,语言成绩好,数学一般,老师说她坐姿特别端正,从不主动讲话,也从不捣乱。放学后王瑶会在图书馆多待一会儿,母亲下班晚,怕她在家出事。她习惯一个人看书,把词汇本记在旧信封背面,晚上回家吃饭、学习、睡觉,日复一日。
十四岁那年,母亲接受洛杉矶比佛利山一户华人家庭的住家保姆职位。对方姓盛,丈夫做地产,夫人是大学教授,讲英美文学。王瑶跟着母亲搬进盛家后院的佣人房,是一间由车库翻新的独立小屋,铺木地板,有简易的洗手间和一张单人床,收拾得干净整齐。盛家对佣人态度温和,说话不重,只是不亲近,也不鼓励越界。
王瑶继续通勤到原来的公立初中,每日放学后从厨房侧门回后院,绕过泳池,直接进屋。母亲提醒她:“盛先生和盛太太人很好,但我们是雇员,懂分寸就好。”王瑶照做,从不在主屋久留,只用厨房边门进出,从不进入私人空间。
盛家的儿子盛轩和她同龄,就读Harvard-Westlake,是最好的私校之一。盛轩每周有两次网球课,周末请家教补数学。两人偶尔在后院擦肩,见面打招呼,有时她在外面背书,盛轩从球场回来,会顺手问一句:“你在准备什幺?”或者“你每天都走着回去?”
她母亲总说:“不要和人家孩子太熟。”王瑶听得进去。她不主动搭话,也不多停留。她的生活节奏清清楚楚:早起上学,回家复习,背SAT词汇,做账本,帮母亲把采购单重新算一遍。
节假日时,盛太太会送她一些旧书、礼品卡或者剩的欧洲进口饼干,说:“这些太甜,你们尝尝。”盛先生也常在晚饭后顺口问一句:“最近课业忙吗?”王瑶每次都点头,说谢谢。他们有礼貌,有距离,不故意亲昵,也不把人晾着,始终维持一种克制的温和。
王瑶有记日记的习惯,把日常细节一笔一笔写在软封本里。她记录每周垃圾车什幺时候来,盛太太几点出门上课,盛轩晚上在哪个时间段会在泳池边讲电话。他总是走来走去,语速不快,有时夹杂一句中文、有时是低声笑。她坐在佣人房窗边,看着他在玻璃门前走过一圈又一圈。
十五岁那年夏天,盛家提出带他们母女一同去马里布海边过周末。王瑶起初拒绝,说自己不爱下水。母亲劝她:“人家请你是看得起,别太僵。”
王瑶穿着旧连体泳衣,披了件衬衫坐在沙滩边。盛家带了帐篷、便当、果汁,还有两只防水音响。盛轩在水里跟朋友打水球,水线不远处传来嬉闹声。
王瑶坐在石头上,背对阳光,脚边是母亲收拾好的便当盒。突然一声尖叫打破节奏,浪高起,一个人影翻进水中。岸边的人群开始移动,盛太太喊:“轩轩!”
一个游客跳进水里,把人拖上来,湿发贴在脸上,脸色发白。王瑶挤到前排,蹲在盛轩身边递纸巾,盛轩吐了一口水,睁开眼看着她。
盛太太扑过去抱住儿子,眼睛红了,随后看见王瑶,伸手握住她的手,说:“谢谢你。”
她没解释,也不知道该怎幺说。那一刻,没人在意过程,只看见结果。
那之后没几天,盛先生提出将王瑶转入Harvard-Westlake。费用、手续都由他们安排。她母亲想了三天才答应。盛太太说:“不是还恩情,只是觉得她这样浪费了太可惜。”
私校的第一天,王瑶穿新制服、旧球鞋进校门,站在教学楼前发呆。教室是冷气恒温的,讲台背后挂满各年级竞赛奖状,学生桌面干净,墙角摆着三脚架和实验模型。
老师介绍她时,同学们礼貌点头,没有人多看。课间大家讲起出国营地、骑马夏校,用的是她听不懂的语调。午餐时间,她拿出带来的便当坐在角落,餐厅另一头有汉堡、沙拉、自选热汤,她不知道该怎幺点,也不想问。
放学时,盛轩走过来,把一袋文具和记事本递给她,说:“有些东西你可能还没准备。”
她接过,说谢谢。盛轩点点头走了。那天下午她回家,把袋子放在书桌上,坐了很久。
她心里确实动了一点。他穿着深蓝校服,头发被太阳晒得微褪色,背光站着,有点好看。她知道不能多想,就把那种感觉压下去。她明白这段关系是偷来的,她配不上。
过了两个星期,午后自由活动课结束,盛轩站在教学楼前,有五六个女生围着,说笑不停。其中两个穿的是拉拉队队服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王瑶站在不远处,抱着作业本,原地站了快五分钟。然后她直接走上前,拉了盛轩的书包一把。
“你爸妈让我们早点回去。”
盛轩回头,皱了一下眉,但没说什幺,跟着她走下楼。
王瑶走在前头,心里没底,脸发烫。走到校门口,她才意识到自己什幺都没想好。
上车时她坐在后排。车开出校园,沿着Mulholland Drive缓缓下坡。加州阳光透过窗户打在车窗,整个城市像被晒熟了。盛轩从前排后视镜里看她,第一次认真地看。
她今天穿得普通,头发扎得紧紧的,后脑几缕碎发翘着,脸上还有没褪干净的羞意。
盛轩盯了一会儿,没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