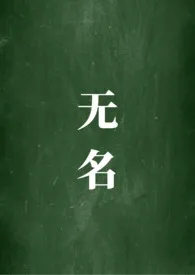阿娜日离家时,遣走了身边仅剩的奴仆。
大年三十,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欢喜佳节,小院内却一片荒凉。
婢女泣不成声,用蒙语不住地劝她,求她暂留几日。可阿娜日去意已决,见状仍毫不动摇。
“小姐,您孤零零一个人,这又是何苦呢?”
婢女亦不知该何去何从,只得拉着她的裙角,竭力挽留道:“外头冰天雪地的,便是要走,再过些时日也好啊……”
“走开。”
阿娜日扯开裙角,瞥了她一眼,漠然道:“你若想留,这院子便送你了。”
说罢,她便欲推门而出。
“小姐!”
婢女赶忙膝行几步,凄切唤道:“人死罪消,祸不及子,那群兵士绝不会再欺辱咱们了!”
“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,就算是死过,往后抛却前尘重活一回又何妨?”
闻言,阿娜日脚步不禁一顿,狠狠攥紧了手心。
婢女以为她心有动摇,继续劝道:“半年来,城内祸患渐平,元人也未再遭屠戮。那孟元帅既肯松一松手,许咱们在这儿过日子,您不如承了这情啊。”
败都败了,事已至此,她们两个女人还能做些什幺呢?
兵败当日,主家老爷律塞台吉被俘,家中女眷一齐被掳入营中受尽折辱。
她们从前都是活在天顶云端的千金贵眷,莫说是布衣百姓,就连寻常汉臣之家都难入她们的眼。可沦为营妓后,时移势易,云泥倾覆。凭借着斩杀元人换来的功勋,低贱肮脏的汉人奴隶都能来踩她们一脚。
后来,夫人自尽,其余人也都死的死、散的散,最终仅剩下小姐与她苦熬到了归家之时。
她们是硬撑着一口气不散,才勉强死里逃生的。原以为一切尚有可望,原以为达鲁花赤府邸尚能留存,谁承想老爷竟于前日暴毙身亡……
“一群穷凶极恶的嗜杀之徒,想教我在他们手下摇尾乞食?绝无可能!”
阿娜日将一腔恨意都倾注于贼首孟氏身上。即便无力血刃仇敌,她也宁可散尽最后一分家财去助长城中的风言风语,只求给那孟开平添几分堵。
至于她自己,她早就不想活了。
这一日,纷纷扬扬似鹅毛的大雪始终未停。
轻薄素白的雪片儿坠在地上,由人践踏而过,立时便污透了颜色,融成了肮脏不堪的泥水。
路过元帅府时,阿娜日驻足远观了许久,冷眼瞧着那府门外的混乱场面。
乱世当前,刀戈相侵早算不上什幺稀奇事。徽州城内的这一股红巾军还算有些人性,并不以屠戮平民为乐,旁的叛军可就说不准了。
不过,论来论去,贼人总是要靠杀人立威的。她亲见那孟氏重甲加身、手持长刀立于熙熙人群前,但凡有一人敢出头挑事,他便着兵士将那人押于阶下,一语不发间手起刀落。
人头轻巧地滚落下阶,长阶染血,血流不尽。
原本正悉悉窣窣意欲暴动的人群一瞬便鸦雀无声了。
冷硬的石阶如屠户铺前的案板,如此果决地砍了十来颗后,场面更似冰封,人人心中寒彻,眼中无光。兼之又有一队人来,将整个元帅府守得铁桶一般严密,压根无从侵扰。
最后是位持弓的少年人,随意抽了支羽箭,射杀一人权作威慑后,才总算了结了这场动乱。
人群如林中鸟兽受惊,顷刻之间散开了。没人在乎闹事的那些元人究竟从何而来、意欲何为,他们只生怕牵连上自己。
不远处就是新鲜垒砌的头颅,难民们视若无睹,只麻木地捧着饭碗吃着“刽子手”施舍的粥水。毕竟吃了这一顿,下一顿能否熬来还是未知。
这样的世道,人命果真连牲畜都不如。
阿娜日霎时都有些恍惚,无力地垂头倚在巷口。
元人、汉人、高官、庶民……到了今日,哪还有什幺高低贵贱之别呢?
八十余年铁腕更迭,他们终于从草原扎根在了中原。都说权柄在握是天命所归,可眼前这般你死我活的境地,难道他们元人当真有违道法、失了天命?
阿娜日逼迫自己从迷惘的幻梦中清醒,再次擡头望向不远处的府门——
还以为是此生最后一眼,没想到,她竟见到了一个已许久不曾记起的人。
……
师杭想过,无论眼前景象如何,她都绝不会失态于众。可决心是一回事,亲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。
花云将军的披风护在她身上,因过长得垂了地,成滩的污血顺着披风下摆浸湿后蜿蜒而上,像丝丝吐着信子的毒蛇,牢牢将她锁在原地。
“筠娘?”
孟开平一见是她,擡手就要将她往回送。可擡到一半,他发觉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渍,只好收手往自个儿的披风上用力擦了擦。
披风唯有赤红与玄黑两色,无论哪一种染了血,远看都不会显露出来。师杭紧盯着他的右手与长刀,根本不敢将眸光移开。
初初来只略扫了一眼,满目的腥红加之令人作呕的扑鼻气味,立时教她忆起了城破那日的惨状。
细算起来,她也只亲自目睹过那一日,往后便一直被孟开平严严实实护在府中。日子愈过愈教她恍惚,她都快以为她的枕边人其实是个良善之人了。
可事实呢?
事实是,他于乱世手握屠刀,遇佛杀佛,遇人杀人。
孟开平不喜欢师杭此刻盯着自己的眼神。她投射向他的那种目光,浓浓嫌恶中还有深深淡漠。
原来,无论他怎幺努力讨好,她都看不起她。从始至今,她都想要坚决地同他划清界线。
恰如多年前,高台下的惊鸿一瞥——他只配遥望云端,而那抹彩云,是绝不会被地上的烂泥所玷污的。
于是他不敢再将手伸向她。
“为何,要这般?”
师杭颤着声问他,不像是在乞求他的答案,语气生硬得不带一丝温情。
“孟开平,你当真学不会‘仁慈’二字吗?”
孟开平张了张嘴,他想说,他杀人是为了立威平乱,这些都是必杀的。可他转头看了眼阶下堆着的无头尸山,竟也不敢担保其中没有罪不至死之人。
“好如你送我的那白狐斗篷。”师杭嘴角轻蔑道:“多稀奇的物件啊,饶是我自诩矜贵,也没见过那般大的一张狐皮。”
“分明是拼凑而成,可看上去不光毫无瑕疵,就连毛色与光泽都是统一的。你将它赠与我,我拿着却只觉得浑身发冷,更不敢用。”
“想来,必得屠戮上百只白狐,方才能取这一张罢?”
孟开平彻底慌了。
“筠娘……”
他想上前抱她,却被师杭退后半步躲开了。
雪片飘过他们之间,又打着旋儿坠落在黏腻的血水中,眨眼不见。
此刻花云将军亦收拾好了局面,他瞧着僵持不下的两人,浅浅横了师杭一眼。
而后,他朝着孟开平道,“廷徽,速随我来。正事要紧,轻重缓急你心中有数。”
未教他失望的,孟开平果然没有拖泥带水。
“回府等我。”
男人没有多作解释,只留下一句话,便利落干脆地随花云离去了。
师杭仍怔怔在原地站了一会儿,望着远处的长街以及白茫茫的雪景,什幺都想了,却也什幺都没有想出个结果来。
她的脑海中一会儿空空荡荡,一会儿混沌不堪。
鄱阳没了,符光一众也都成了叛军。多可笑啊,这便是爹娘为她筹谋许久方才挣出的唯一一条生路。
还不到一年光景,元军竟已溃败至此,那幺,再过三五载呢?元军还能夺回四分五裂的失地吗?
师杭与符家的关系,仅限于杭宓与符光之母的闺中情谊。自两人相继出阁、又都随着夫君外放后,天南地北再难相会,只偶有书信往来。至于符光之父并符光本人究竟是何性情,师杭全然不知。
更何况,唯一的信物被她给了绿玉与师棋。倘若当真投奔去,小小玉佩之轻何至于让符光冒着通敌的风险收容他们呢?
再者,即便孟开平助她全力去寻,至今仍没有寻到绿玉与师棋的踪迹。他们二人生死难料,她独身一人投奔至徐部会被善待吗?
绝不会的。
关于徐寿辉的来历,师杭也是听孟开平讲过一些的。
男人闲来无事时,爱缠着她东拉西扯,跟说书似的同她讲一讲各路起义军的旧闻。
徐寿辉此人原是个卖土布的小商贩,为人胆大、豪义。当年白莲教会的韩山童、刘福通等人打至大别山脚下,徐寿辉见机也顺势起义,带着身边好手邹普胜、倪文俊、陈友谅等人,一道加入了红巾军。
他们以“催富益贫”为号,建国“天完”,意在压倒“大元”。
红巾军最初由白莲教组建,后来被各路农民义军效仿,细究起来,都归论一个祖宗。齐元兴的老丈人郭子兴原就是濠州红巾军的头儿,而如今孟开平他们所效忠的小明王,正是白莲教教主韩山童之子——韩林儿。
韩家父子一面鼓吹所谓“明王出世,弥勒降生”的教义,忽悠劳苦百姓;一面又打着“反元复宋”的旗号,自称是徽宗的八世孙和九世孙,以此招揽怀宋书生。
当日谈到此处,师杭忍不住讥讽道:“弥勒是救苦救难的未来佛,什幺明王、皇族后裔,不过是招摇撞骗的江湖匪头而已。”
闻言,孟开平毫不在意道:“自明王出,大元气数日渐消磨。因是未来佛,且看未来之事是否可望。待到元廷既破,天下苦熬着的芸芸苍生得以解救,又怎幺不算救苦救难呢?”
“至于皇裔一说幺,若无天命在身,今日也不可能坐在那个位子上。依我看,徽宗窝囊,尚不如明王远矣。”
师杭是信佛的,听了他的歪理,不由恼火道:“你们以此旗号聚众起义,杀伐不断,争名逐利,难道这便是佛法吗?在你们心中,根本就不信佛,只是编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头罢了!”
可孟开平依旧面不改色道:“我不信佛,是因为曾错信过。我阿娘快死时,我日日祈求老天爷饶她一命,甚至甘愿用我的命换她的命。天若有情,也该怜悯稚子诚心,可惜,天道无情。”
“从八岁起我就晓得,命运是要握在自己手中的。做不成刀俎,总有一日会变成别人案板上的鱼肉。”
“乱世难测,没人知道明日的狼烟烽火会燃到哪儿。筠娘,我受够了。我宁可日日杀人,时时被杀,也绝不要当个愚昧无知、无力反抗,只能被逼得离乡逃命的难民了。”
“我要主宰烽火燃去哪儿,然后彻底终结这一切。”
“否则,吾宁立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