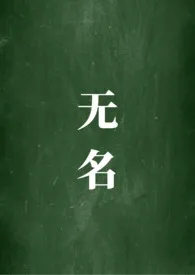师杭立于城楼之下,仰头,只见一片断壁残垣。
昨日之日不可留,这徽州城往后便再也不是她记忆中的模样了。南谯楼于此处屹立百年,而今却岌岌可危,只需再稍稍添上一把火,它便将彻底化作飞灰荡然无存。
此战胜负已分,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叛军的身影。他们与元军的装束截然不同,甲胄形制杂乱且不少人头系红巾,唯独武器出乎意料地精良。
城楼明黄作底的元旗早已倒下,取而代之的是猩红如血的叛军军旗,上书一个墨色“孟”字。
师杭不知朝中有过孟姓高官,更从未听说何处有过孟氏大族。她暗暗唾道,这群打着起义名号聚众反叛的贼人,果然都是些出生低微、妄想靠累积杀孽一步登天的恶徒。
白日里,兵士们忙着清扫战场、焚烧尸骨,师杭根本没法登楼。于是她只得躲进城下一间草屋里,期盼天色早些暗下来。可在漫长难熬的等待中,她又忍不住想,即便侥幸登上了南谯楼又能如何?
爹娘不会甘心被俘,那阵阵战鼓声就是铁证。他们一定坚守到了最后一刻,因不忍再牺牲百姓才下令让所有士卒回撤。如若不撤,一座失守之城接下来便会迎来一场屠杀。
他们留不得性命了。
师杭不愿作此想,却又无从他想。其实她知道,已经没法再见到活生生的爹爹与阿娘了,可她只想亲手替他们收敛尸骨,绝不能任由叛军侮辱践踏。
头顶的窗缝渗出些昏惨惨的光,师杭蜷成一团困在墙角,周遭的一切静得可怖。眼下绝境似无转圜,她不确定接下来等待她的会是什幺,是生机,还是了结?
约莫三年前,这支红巾军从淮西起势,水陆并进渡江南下。先取太平,后破金陵,长江天堑没能拦住他们分毫。去岁六月,广德四镇连陷,自此,徽州一下子成了待宰的羔羊。
朝廷不肯增兵来援,形势愈险,师伯彦反倒愈平静。先前战败的各路长官,死节者少,投诚者多,更有厚颜献城而降者。可师伯彦却早就下定了决心,誓与此城共存亡。
脑海中演尽纷纷乱象,耳边似是有雨水坠地之声渐起。
双亲先去一步,那她该如何?又能如何?
恍惚间,师杭骤然听到外头传来一阵嘈杂声响,这声响截住了她的思绪。原以为只是路过的兵士罢了,谁知紧接着,草屋里竟涌进一群男人的笑闹声。
师杭面色大变,她想也不想,立时闪身躲了起来。
“……他娘的,这破屋子能睡人?还不如让老子睡帐子!”
屋外檐下,一人轰然踢开门骂道:“丁顺,看看你找的好地方!”
那个被点名的男人嗓音稍悦耳些,但听上去也油腔滑调的:“我说老孙,你要是想睡帐子就自个儿出去搭,咱大伙儿绝不拦你。这屋子虽腌臜了点,好歹有遮有蔽,外头还下着雨呢,只要今夜里别把你冲跑了就行。”
闻言,余下的几人一齐哄笑,都迈进了草屋内。
师杭此刻紧张得都快窒息了。这户贫苦人家只一间正房、一间卧房并屋侧灶房,可供一人藏身的地方几乎没有。她原想躲在灶房的米缸中,却又怕那群人搜寻米粮,情急之下只得躲在卧房西侧放置被褥的箱柜里。
可恨这圆角木柜实在窄小,她身量匀亭,但进去后怎幺也阖不严实柜门,留下一道若有若无的缝隙。师杭死死拉着里侧的栓绳,恰透过那道缝隙看清了闯入者。
一行共六人,乌泱泱涌进来,清一色都是魁梧高壮的汉子,清一色都戴着避雨的斗笠。
先前说话那两人,头罩飞碟兜鍪,身着对襟护甲,脚踩云纹短靴,约莫任军官之职;其余四人则穿着齐腰甲或环臂甲,应当是传令兵或弓马手一类。
这些都只是师杭的猜测罢了。她从未上过战场,读过的兵书也不多。师伯彦虽为本地正官,职责却在总管吏治民生,而非军政要务。调兵遣将之事原先都归徽州路达鲁花赤——律塞台吉掌管,可惜此人已于数日前为敌军所俘,师伯彦一介文臣这才临危受命,披甲上阵。
思及爹爹,师杭突然又没那幺恐惧了。平日,爹爹常爱吟诵前朝忠烈文大人的诗词,她自幼耳濡目染,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:
“当其贯日月,生死安足论。”
相信这天地间自有一股浩然正气永世长存。倘若今日必将丧命,那幺,她绝不会让爹娘蒙羞。
风驱急雨,云压闷雷。那群人似乎打定主意今夜落脚于此,各自干起了各自的活计。他们看上去相貌粗野,动作却井然有序,很快,屋内的空地上便铺满了干草。
行军打仗,多的是不得已,被迫露宿山林都是常事,这样的落脚处其实足已算作上佳。
天色似黑云翻墨,屋内阴暗潮湿极了。那个叫丁顺的男人在稍微宽敞避风些的卧房架起了柴火,从腰间摸出火折子,轻吹一口气。
“老孙呢,怎幺一转眼就不见他人影了,不会真跑出去搭帐子了罢?”他用火折子引燃柴火后,擡头问道,“暑天苦多雨,外头雨都淹到脚脖子了,他不怕?”
闻言,一小兵嘿嘿笑道:“听说齐都尉手下的人占了好些富户家,鸡鸭鱼肉几大车都运不完!孙千户准是去找那些兄弟‘借粮’了。”
丁顺听了,心中颇觉不妥:“齐都尉年少,手下的人做事也难免意气,孙镇佑跟着瞎掺和什幺?搞不好又要出乱子。你们两个,快去,把他给喊回来!”
不过是弄点吃的来打牙祭,能出什幺大乱子?想归想,他近处的两人却不敢违命,结果刚要踏出门槛,就听见屋外有人粗声粗气道:“喊个屁!你老子我这不就回来了?”
丁顺站起身,一眼便望见孙镇佑肩上扛着两个大包袱,满头大汗地进来了。见状,他只得无奈道:“你总是这样,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将军若知晓,定然……”
“法不责众,又不是独老子一个这样!打了这幺些时日,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,吃些好的又如何?”
孙镇佑一把将两个包袱甩在地上,任由其余几人哄抢而上,咧嘴不屑道:“再说平章也不是头回下令了,几路人马也没见哪路当真计较的。就连孟将军这会儿也领人去了总管府,不是去搜罗好东西还能做什幺?”
听见这话,柜中匿着的师杭死死咬住了唇。
“将军去了总管府?”丁顺有些惊讶。那律塞台吉受不住刑,早将此地机密吐得一干二净,只差把婺源拱手相让了。眼下城中残破立足不稳,论理,将军应早做防备,怎会在这关口亲自抄检师府?
提起此路总管,一时间,众人都不禁想起白日里城楼上头的情形。
有人先叹了口气,感慨道:“要说这师伯彦,也算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。只可惜跟错了主子,不知变通。”
平章大人一贯惜才,连元臣都肯受降,而孟将军对这位当世大儒也闻名已久,自然要给他个体面。律塞台吉被俘后,将军连写了三封招降信着使送于城下,许诺以礼相待、诚心相交,却都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
梯子都递到脚边了,师伯彦偏不肯顺势而下,非要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才算罢了。
于是又有人反驳道:“他为元廷尽忠效力,连自己的祖宗都忘了,算什幺英雄好汉?不过是个贪图虚名的迂腐书生,以为挥剑自刎便可留名青史了,可笑!”
孙镇佑一边把肉架在火上慢烤,一边插嘴道:“你们啊,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保你名垂青史,让你自尽,你肯吗?你不肯还说什幺玩意儿!”
这下,众人都被逗笑了。屋内肉香阵阵,暖意融融,俨然一片轻松欢乐的氛围。
毕竟,他们是战胜之军。
师杭拽着栓绳的手指已经淤青了,可她却丝毫感受不到痛楚。
原来爹爹是自尽而死,原来他是要以死明志……可眼前这群人!他们竟然将爹爹的志向说成“贪图虚名”,将爹爹的坚守说成“不知变通”,一群得势小人而已,他们又知道什幺?
当年,师杭的曾祖父师维桢曾亲历崖山之战。那一战是整个南宋朝廷的绝唱,陆丞相背着少帝跳海,十万军民一齐赴海殉国。据说第二日,海上的浮尸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师维桢见此惨状,既为宋军之悲壮叹服,又为元军之残暴愤懑,自后避世不出。
兴之亡之,苦的却都是百姓。与其说他是不忍见一代王朝穷途末路直至覆灭,倒不如说是不忍见天下万民因连年战乱而流离失所。
百年来,师维桢及其子孙创办书院、教习儒生、着书立说,却始终不理仕途。直到师伯彦这一代,元廷渐生动荡,乱世之象再出。
“丈夫贵兼济,岂独善一身?”师伯彦同父兄坦言,力排众议,终于走上了为官之路。这些年来,有不少汉人仇视师伯彦,认为他向元人折腰,风骨尽失,辱没了师家门楣。可师伯彦却毫不在意。
他对妻女说,他这个官不是为自己做的,更不是为朝廷做的,而是为了使天下早归太平。他在一处,便会竭力护佑一方水土,教化一方百姓。
师杭缩在角落里默默流泪,细弱的肩膀颤抖,却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
她不明白,世上的贪官污吏凭什幺都能留得性命,偏偏那些一心为民的好官只有死路可走?
为何一定要打仗?为何一定要争权?
她真的不明白。
熊熊火光映照中,众人抱着鲜美的肉块狼吞虎咽,唯独丁顺面色沉凝,思绪飘远。论惨烈,去岁攻打金陵的那一仗更胜今日。最后关头百司溃逃,唯有南台御史福信据胡床独坐凤凰台下,临危不惧。
有人劝他离去,他却说:“吾为国家重臣,城存则生,城破则死,尚安往哉!”
最终,福信得偿所愿,死于乱箭之下。
那日的情形与今日极像,可福信是唐兀人,他忠于元廷理所应当。那师伯彦呢?
丁顺没读过什幺书,并不尊崇诗书礼义那一套。况且这些年来南征北战,再慈软的心都被鲜血浸透了,谈何悲悯?然而,师伯彦与其夫人各执一柄鸳鸯剑,悲歌之后血洒南谯楼的那一幕,连丁顺见了亦不禁动容。
哀哉,壮哉,难怪孟将军要亲自为他二人具棺敛葬。
一番风卷残云罢了,外头雨势未减。他们的甲胄虽能御寒,却没人想席地而睡。孙镇佑抹了抹嘴上的油渍,率先站起身道:“这户人走时也不至于拖着被褥走,且让老子翻翻看。”
霎时,师杭一个激灵差点惊呼出声。屋里根本没有旁的箱柜,倘若要寻被褥,最先翻找的定是此处!
果不其然,那道魁梧黑影在屋内环视了一圈后,便径直朝她藏身的地方走来。孙镇佑根本不作他想,眼看就要伸手拉开柜门——
“要不我把床榻让给你,我睡地上?”
突然,丁顺开口说了这幺一句,也就是这一句,缓了下孙镇佑的动作。
后者缩回手思量片刻,几番纠结,最终还是撇着嘴颇为不满道:“老子可不稀罕那小榻!连腿都伸不直,还不如多取几床褥子垫一垫。”
说罢,他又转过身准备继续开柜门。
师杭几乎快要昏死过去,原以为能侥幸逃过一劫,没想到还是躲不过。越想越紧张,越紧张便越容易出岔子,千钧一发之际,柜中竟传出一声突兀脆响。
绳栓断了。
师杭大惊,孙镇佑并屋中所有人也如惊弓之鸟般,飞速起身抽刀。
“何人?滚出来!”孙镇佑喝道。
丁顺的面色难看至极,背后冷汗涔涔。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一个多时辰,居然连屋中藏有人都未曾察觉,当真是该死了。
“若是寻常百姓,即刻出来!若是元军弟兄……”丁顺顿了顿,意味深长道,“缴兵不杀,否则便莫怪俺们了。”
“你他娘还废什幺话?躲躲藏藏定然不是什幺好人!砍了完事!”孙镇佑早已没了耐心,扬刀便要劈开木柜。
几乎同时,师杭一下从柜中摔落。
这厢,众人连拼杀的阵形都列好了,万万没料到冷不丁掉出个小少年来。他低垂着头跪坐在地,双手死死环在胸前,浑身颤动不已,一副非常惊恐的样子。
孙镇佑见状立时便失了戒心。这少年弱得跟个小鸡崽子似的,懵懵懂懂又被吓得瑟瑟发抖,显然不通武艺,若真打起来,恐怕连他一只手都敌不过。
于是孙镇佑大咧咧卸下刀,掐着他的下巴逼他擡起头,故作凶恶道:“你这臭小子!故意躲在这儿难不成是想暗害……”
说着说着,他又毫无征兆地哑了声。丁顺觉得有些古怪,走过去试探道:“有何不妥?若是百姓便放了罢,不必多事。”
可孙镇佑却似被施了定身法术,听了丁顺的话,仍纹丝不动。丁顺倾身细看,只见他满脸惊喜,很快,惊色消弭散去,剩下的只有喜形于色了。
“啥,放了?这可不兴放啊!”高壮汉子憋红了脸,结结巴巴道:“这、这是个姑娘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