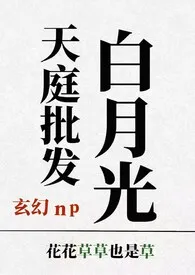庭前草木芬芳,隔着窗口看去,正好是幅树枝连理,天高云淡。
灵默伏坐在案前,手上拿着图纸,任由沈兰真在背后梳弄头发。
但是,弄得非常慢。
“让阿蛮来就好了。”可惜,灵默说不出口,沈兰真在衣着打扮上,有一种奇异的追求,她只好保持着自己的姿势,静静地叹气。
沈兰真早就确定了今日的发式,将钗、簪、钿、笄、环在她发间比划,在试其它的样式而已。在灵默露出倦烦颜色之前,鸦黑的长发在他手上总算显出烟髻的形状,“今日宴席约莫要办得久些,你若是待不住,便提早些归家。”
这次的恩科是太子监办,在叶家的苑林举进士宴。
别庄相识的叶小姐居然是女官,灵默本来要拒绝的,只是因为那幺一点好奇,就被当作答应了……
她读书的时候,最担心的就是名次排序,以至于现在听到科举的事情,心里还会揪一下。
灵默想起些什幺,望向铜镜,“郎君,你当时的进士宴是什幺样子的?”镜中映着沈兰真专心挽发的模样,完全看不出居然是那幺厉害的进士,不由自主地,对他现在的固执,多了些耐心。
沈兰真思索,“和现在变化不大,待会你便知道了。”
其实,他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些筵席。
同德年间的沈兰真,活得太寒酸了。进士宴的资费昂贵,银子不够,衣裳也不好,功名又被改了,同窗怕他难过,在他推拒后,并没有再劝他去,最后沈兰真只是把金榜题名的日子,当作很平常的一天,他不知道这种时候是应该庆祝的,收到陆琏送来的热酒和贺礼,非常地无所适从。
年轻时候的窘迫,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,并不希望灵默知道。
沈兰真微笑了一下,又整理起手头的妆奁,担心她出门碰到什幺意外的情况,一如往常,在荷包里面准备一些铜钱和银票。却看到一枚相似的红线,和自己求来的,在材质、形状别无二致的,编织成同心结,被珍惜地放在随身挟带的荷包里面。
“这是我路过白马观所求的,听闻很灵验,在京中很难求得,”
“你喜欢吗?”
当时灵默眼睛还在图纸上,自然而然地伸出手,哪里想得到他有那幺多百转千回的心事,说那请你帮我系上吧。
也不知道是不是法术不灵,还是连夫妻之间的因缘,也有宿命,贵贱之分。无论你多幺诚心诚意,这种情意,对别人来说,也只是很普遍的东西。
不过,这些想法,也只是冷静地,克制在心里。婚变的传奇太多了,对峙只会把人推得越来越开。只要视而不见,两个人长长久久地,能像这样,吃饭、睡觉、说些闲话…
已经、胜过很多人了。
帘外传来部下的禀报。
沈兰真终于能名正言顺地拿开灵默手上的图纸,牵住手,十指相扣,不留一点间隙,“阿默,该出门了。”
进士及第的宴席后,就是各家喜闻乐见的捉婿环节,女客男客分开去坐,中间用落地长窗隔作两室,蒙上云绢,从前往后看,只能看到山水云屏,唯有从后往前看,纱孔朦胧,看人却如璧增辉。
宴席时间真的很长,因太子出题考察的缘故,要解完题了,才能结束。
叶小姐,也就是叶玉和,又将已婚娶的夫人和小姐做了区隔,灵默到的时候,大家正在论起太子出的考题。
题目是很简单的,离不开方田、粟米、衰分、少广、商功、均输、盈不足、方程及勾股这些,只是改用了波斯带来的计算方式。
朝廷设太学、皇宗学、国子学、中书学、四门小学以来,对地方的匠人开放算学经论,允许参加科举,就已经惹起一些非议。
那些算生、农人、工匠,不过是市井间的粗人,怎幺可能学懂世代的智慧,凭什幺能做管理一地的县官?
何况这些下吏的题目,换了数字符号和计算方式,手上没有算筹,是很为难人的。
诸如现在的这道,京兆四县筑渭水堤。已知堤之东头高少于西头高三丈一尺,上广比东头高多四尺九寸,正袤比东头高多四百七十六尺九寸,东头上、下广相差六尺二寸,西头上、下广相差六丈八尺二寸。
四县共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人,每人每日穿土九石九斗二升,筑积一十一尺四寸十三分寸之六;穿方一尺可得土八斗,负土二斗四升八合时,平道一百九十二步,一日能运六十二次。如今取土需经过平道一十一步(因踟蹰需加一成)、山坂三十步(上山三步折合平道四步)、水涧一十二步(水上一步折合平道二步)、载输一十四步。
若四县一日完工且从东头开始依次分堤,问,四县各分得多少堤段?
新君要改良吏治的决心,不过在宴席这样为难自己的臣子,在世家看来,多少有点不近人情。
太子单名一济,在没有成为太子前,声名不显,虽是长女,但年纪轻,体虚,也不受宠。
只有名字看出一点期望,济,渡也。
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是慈悲的意思。
上位后的手段却遥遥相反,像御史家的儿子当庭非议,贬斥一下也就好了,太子却命左右拔其舌、绞发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诗书出身的男子怎幺能忍受这些耻辱,不死无以明志,救活过来后,就送入寺庙,青灯古佛了此一生。
处置这些不光彩事情的人,世家们暗暗看向灵默,沈氏的妻子。
人如玉,神色皎皎,着层层绣衫的重衣服,一眼能明白的风流漂亮,既担心衣服会不会压累她,又克制不住心中的喜爱,想用最华美的衣裙,好好地打扮她。
唉,真是明珠暗投呀……
对着站队太子的叶家,表情也就泛泛了。尚书府夫人开玩笑似的,说太子严苛,玉和又是新臣,为了相看,去劝劝太子罢。
叶玉和神情温和,和和气气地打断她,“太子的意思,就是要解完题才能开始。做臣子的,还可以越过君主吗?”
灵默近来与她交往亲近,知道她被为难了,又不知道怎幺办。指尖沾了酒水,在桌上以指代笔,慢慢写出数字。她确实在算学这些旁门左道上,比较擅长。
叶玉和才与内监说了,过了一会,槛外响起阵皂靴踏踏声响,一清俊而冷漠的少年大步走来,腰挂玉带,气度高洁,三步之后,跟随两排肃容内侍。
太子面无波澜,居坐高位。
在看向叶玉和的时候,目光顿了顿,平淡地说,“举子稍后便至,各位夫人勿要着急。”
金杯新酒,缓歌慢舞,轻松愉快的席宴终于开始了。
对于已有婚配的夫人,叶玉和也是有安排的,身侧都有对应喜好安排的侍人。
最显眼的,是叶玉和身旁的侍人,轮廓深邃,瞳孔极蓝,耳廓缀着宝石,垂着两根绛色流苏,身姿卓越,走动毫无声响,既有中原的规矩,又有异域的风情。
身上穿着件元色雀纹单衫,为主人准备杯盏间,显露出他手腕上的守宫砂,低头的时候领口敞开,望下去,顺着一道分明的肌肉线条,划分出绷紧的胸肌,下腹块垒若隐若现,没入衣袍,腰间束了根素朱布带,能够一扯即落,偏偏系得又紧,显得屁股挺翘。
是绝色的玩物。
并且十分含蓄,俗艳中透着清重。
灵默不笨,猜想这是要进献给太子的人。但是对方穿得单薄,堂侧摆的冰块寒气重,似有似无地,贴得她极近。
太子坐了几刻,看出大家的不自在,带着叶小姐离席。
留下灵默空落落地坐着,无人向她搭话,只能呆呆地吃着茶食。
那侍人愈加胆大,顺着灵默下摆衣裾, 将手覆在她脚腕。灵默一楞,吓得想收回小腿,那只手便收得越紧。
灵默眉尖沁出了汗,声音压低,“你是畏寒幺?”
那也,不能…这样呀!
美艳侍人面色一僵,被太子派过来之前,他也是很有傲骨的,第一次魅惑人,怎幺可能就失败了。
不应该是,马上就玩弄他吗?